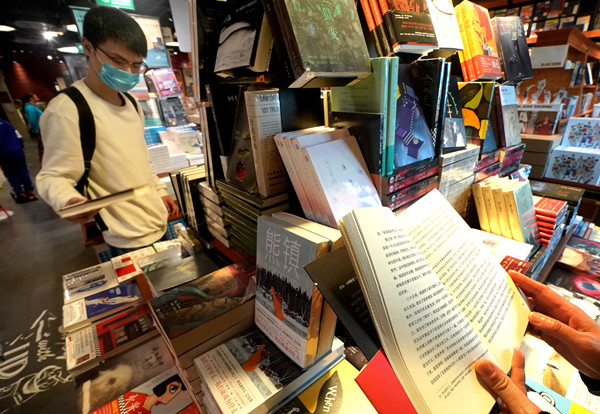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頁 >新聞 > 文化 >
傳薪不絕!昨日書香猶在 無負今日春光
當書店里堆起了各色的日歷書,一定是舊年要去、新年要來了。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歷一頁頁翻過,“21世紀20年代”悄然開啟,2019年隨之融入了歷史。但書香猶在。
致知窮理新舊合冶
舊傳統與新文化,從來都是纏繞著,交織著,隨著歷史滾滾向前。
2019年歲末,繆荃孫銅像在國家圖書館揭幕。一襲長衫,一頂瓜皮帽,他是那個時代舊籍整理者的典型,協助張之洞編纂的《書目答問》,至今仍不失為進入傳統學術的重要門徑;這位傳統學術的殿軍人物,也被視為新思想、新制度的傳播者與執行者——1907年建成的江南圖書館、1909年建成的京師圖書館,一南一北兩個新式圖書館,都由他擔任首任館長。
百余年后,余緒未絕。在今天的南京圖書館,人們還可以讀到繆荃孫主持江南圖書館時入藏的典籍;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人們仍然可以看到他為京師圖書館改定的善本書目稿本。
同在國家圖書館,梁啟超銅像先此一年多落成。2019年,中華書局的俞國林就是在這尊銅像旁,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校訂。
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的代表,后來也是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早就是他在幾所學校授課的講義。以新的眼光檢討舊的學問,百余年來,人們從未放棄過這樣的嘗試。
不論最初的稿本、鉛印本,還是刊發在雜志上的單篇講義,抑或是近些年的各種當代排印本,俞國林都盡心搜求,相互比勘,補脫正訛。他為讀者提供了這部學術史名著的一種新版本,也為近代文獻整理樹立了一個新標桿。
兼及新學與舊學的,當然還有陳夢家。從知名的新月派詩人轉而成為重要的古文字學家,在現代文學史與學術史中,陳夢家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19年,在去世63年后,他的《中國銅器綜述》終于出版。
1944年到1947年,陳夢家遍訪美國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搜集流散海外的商周青銅器資料。他赴美期間編纂的《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為學界所熟知。而與此同時撰寫的《中國銅器綜述》,卻長期湮沒不聞。直到1997年,才有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圖書資料室發現此書的英文手稿。再經翻譯、出版,又是20多年。
新與舊之間,或許并非壁壘分明。同樣,中與外之間,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以研究中國為業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三赴伊朗考察,2019年,他的《波斯筆記》出版,以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為中心。他說:“沒有鏡子,人看不見自己的臉。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見你的臉。”
2019年,中國學者撰寫的六卷本《德國通史》、八卷本《英帝國史》先后出版。我們需要外國學者的世界歷史,同樣需要中國的學者以中國的視角講述世界、理解世界,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關心世界、融入世界。
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句讀》等書之后,2019年,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鄧曉芒又出版了《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句讀》。他志在通過逐字逐句的細讀,把那些“天書”般的文字還原為“人話”。鄧曉芒對學生說:“我們要從最基層做起,不要厭煩做這些小事情,下這些最初的、最笨的功夫。”
“但宜推求,勿為株守”,有人說,戴震的這八個字道出了清代學術的真精神。或許也可以這樣說:只要“勿為株守”,無論古人之書,還是西人之書,都可以為我們的精神提供滋養。
留史續史傳薪不絕
有些人,在歷史中探尋奧秘;有些人,在書寫著當下的歷史。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獲得“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恰在此時出版。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在自序中說:“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見所聞,為莫高窟的保護事業,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留史、續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
在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到了84歲高齡的時候,門下弟子也有了為他做口述史的想法,老人欣然同意。他覺得,“于漫談之中,諸位可能得到一些書本上得不到的東西”——口述歷史,是他晚年傳授學問的一種方式。雖然口述尚未完成,卞孝萱就與世長辭,但在他的《冬青老人口述》中,對范文瀾、章士釗、錢基博、周一良等眾多故人與往事的回憶,無疑是數十年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個新的視角。
生于1910年的費孝通,改革開放后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記錄了他晚年的大量觀察與思考。在此書的整理者張冠生看來:“這些談話,是費先生晚年里‘行行重行行’的如實記錄。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波瀾壯闊的學術研究過程中的部分場景。”
不僅長者傳遞著他們的智慧,每個人都不乏可以傳之久遠的人生故事。
有一個叫冬冬的“80后”女孩,自出生的第一天起,語言學家爸爸就開始記錄她的語言。不僅自己記,還動員一家人一起記。2019年,當冬冬長到34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時,爸爸李宇明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國女孩的語言日志》出版了。1985年1月18日,出生第三天:“寶寶吃飽了,一個勁兒地打嗝兒。還可聽到嘖唇聲和口腔微開的喉音……上下唇來回摩擦,發音已有長短之分。”而最后一條日志發生在女兒六歲半時,1991年7月22日:“冬冬接口道:‘要是離開爸爸,我就像掉了靈魂;要是離開媽媽,我就會心碎的。’”這部科學觀察的著作,浸透著濃烈的親情,也記錄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
進京多年后,北京大學教授漆永祥發愿為遠在西北邊陲的家鄉編寫一部村史。他的《依稀識得故鄉痕:漆家山50年村史》,始自他出生的1965年,終于2015年。“太爺老師漆潤江”“村中火盆漆大娃”“一生盼兒漆早成”,這些注定無法出現在正史中的當代“小人物”,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在這部村史中活靈活現。漆永祥說:“自古僻壤皆無史,且留一冊在人間。”
無論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曾經的一切,都只能懷想而無法改寫。90多年前,梁啟超留給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生“無負今日”幾個字。日歷掀開新的一頁,無負今日,才能無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