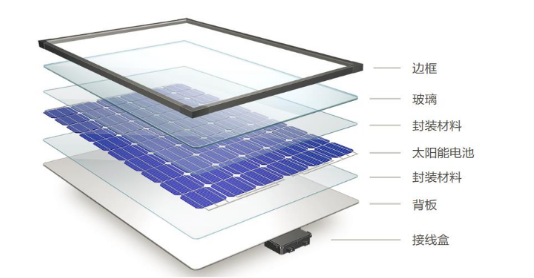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頁 >新聞 > 股票 >
恒銘達低價轉讓股權遭疑貓膩 實控人弟弟借款沒還清?
恒銘達(002947.SZ)今日巨量換手,此前該股連續6個交易日一字漲停。截至午間收盤,恒銘達報47.77元,漲幅9.99%,成交額8.12億元,換手率57.59%。
2月1日,恒銘達于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開發行股票3037.80萬股,發行價格18.72元/股,募集資金總額為5.69億元,扣除發行費用4240.51萬元(不含稅)后,募集資金凈額為5.26億元,用于電子材料與器件升級及產業化項目。

恒銘達IPO可謂是一波三折。去年8月21日,證監會發布公告,鑒于該公司尚有相關事項需要進一步核查,決定取消發審委會議對該公司發行申報文件的審核。11月13日,恒銘達再次上會,獲證監會審核通過。
恒銘達上市發行費用總額4240.51萬元(不含稅),其中,保薦機構國金證券獲得3609.24萬元,大信會計師事務所獲得審計及驗資費用56.60萬元,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獲得律師費用64.15萬元。
恒銘達主要從事消費電子功能性器件、消費電子防護產品、消費電子外盒保護膜的設計、研發、生產與銷售。
恒銘達毛利率變動趨勢與同行明顯相悖。2015年至2018年1-6月,恒銘達主營業務毛利率分別為36.62%、40.53%、47.21%、44.19%;同行均值分別為32.45%、30.32%、30.33%、26.79%。
2015年末至2018年6月末,恒銘達應收賬款余額分別為1.36億元、2.21億元、2.44億元、1.58億元,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44.52%、69.25%、54.22%、80.33%。
外界曾有聲音質疑恒銘達股權轉讓存在利益輸送的嫌疑。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16年11月,在第三次股權轉讓中,恒銘達有限除引入荊世平一人出資設立的恒世達、員工持股平臺上海葳城及恒世豐,還引進了張猛、常文光以及王雷三個自然人股東。三人分別獲得恒銘達343.2萬元股權、214.5萬元股權、83.66萬元股權。
本次股份轉讓對價為2.36元/股注冊資本,張猛、常文光、王雷以其自有資金支付股權轉讓價格,以此價格計算,三人分別需支付809.95萬元、506.22萬元,197.44萬元。轉讓價格參照2016年9月30日恒銘達未經審計的凈資產扣除2016年10月分紅款后的凈資產額為作價依據。
2017年3月,恒銘達以每股約10.06元的價格引入海通開元,海通開元以現金3500萬元認購新增股份347.8萬股,參照標準為增資后恒銘達投后估值。值得注意的是,海通開元與恒銘達早在2016年1月就簽訂了增資協議,只是當時認購資本與之后有所出入,每股價格約為9.78元。短短數月,股份價格差了3倍。
據公眾號“明杰點金”,2016年10月,恒銘達實控人之弟,董事、總經理荊某向公司歸還被其長期占用的累計金額高達2837.48萬元的拆出款項,而公司2016年現金流量表相應科目金額卻反映他僅歸還了2539.72萬元,還有297.76萬元沒有歸還到位。但是,從招股書的文字說明和資產負債表中的財務數據都顯示,當期該項其他應收款已經全部清償,這是一個明顯的數據沖突,或需要公司給出解釋。
據價值線,那么上述297.76萬元的差異是否源自于身為董事、總經理的荊某,根據恒銘達開展業務的需要,作為用于高管開展業務的日常經費而留存下來了呢?好像也不是。根據招股書披露,荊某“拆借公司資金主要用于房產購置、子女教育等大額資金需求。報告期內,荊某與公司的供應商、客戶不存在資金往來。”
此外,有沒有上述還款差額是荊某僅向恒銘達歸還本金,但是資金占用費計入利潤表財務費用的相關科目,作費用化處理的結果呢?結果或許依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上述公司在2015年和2016年兩年中計提的資金拆借費用,合計金額為207.68萬元,與荊某少向公司支付的還款差額297.76萬元相比,相差90.08萬元,不是一個數據。
無論如何解釋,荊某在2016年10月向恒銘達歸還的原先拆出的資金,其現金流量表的數據與資產負債表的數據嚴重沖突,也與公司的信息陳述不符合。
據價值線,通過天眼查發現,報告期內恒銘達的關聯企業不少都注銷了,包括深圳包材、昆山鼎圣達紙制品有限公司、昆山恒富達電子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昆山金鈿文貿易有限公司、東莞市三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武漢包材。
值得注意的是,昆山鼎圣達紙制品有限公司和昆山恒富達電子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的經營狀態為“吊銷,已注銷”,從工商局得知,此種類型屬于先被吊銷后注銷。恒銘達董事長荊天平先生曾為兩家公司的法人。
然而恒銘達在2017年9月提交的招股說明書中對于相關信息可謂是只字未提,在證監會質問后,更新招股說明書中稱昆山鼎圣達紙制品有限公司和昆山恒富達電子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是被“注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