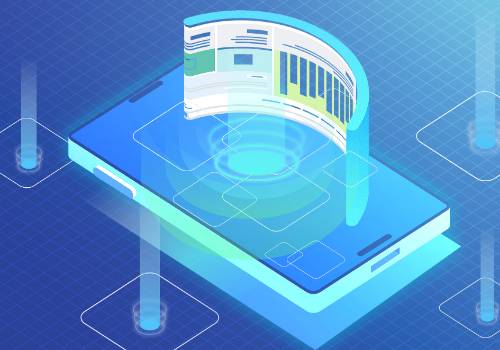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頁 >綜合 > 財經要聞 >
有的發40個月年終獎,有的負債幾十億美元!都是行業巨頭,差別為何這么大?
封面圖 |《海洋之城》劇照
 【資料圖】
【資料圖】
文|風馬牛 (微信公眾號:馮侖風馬牛)
01
「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
按照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的預計,全球人口在前天(11月15日)達到了80億。然而,蕓蕓眾生,悲歡并不相通。就拿「大廠打工人」來說,最近這些日子,有些人歡喜,因為年底即將喜提60個月年終獎,也有不少人憂——要被裁員了。
據《紐約時報》11月14日報道,電商巨頭亞馬遜計劃最早從本周開始裁員,約1萬員工受到波及,這將是亞馬遜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裁員。
不獨亞馬遜,近來多家美國科技公司宣布裁員。社交網絡巨頭Facebook母公司Meta曾于11月9日宣布將裁員1.1萬人。馬斯克入主推特后,也有推特公司裁員50%的消息傳出。
「硅谷大廠」紛紛裁員,理由各有不同。但歸根結底,還是科技公司業務增長變慢,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同時對未來的發展趨勢預期悲觀,于是縮減各方面開支,尤其是人力成本支出。
與普遍感受到「寒氣」的科技公司不同,也有一些行業在疫情之下依然活在鮮花著錦的好日子里。
日前,有臺灣媒體曝出,長榮海運公司今年前三季大賺3000億新臺幣,因此被業界傳出年底有望給員工發出60個月工資的年終獎。
雖然長榮海運對此回應稱,全球貨柜輪市場變動大,現在談年終獎金還太早。但分析人士認為,鑒于長榮海運今年的利潤穩創新高,以及其前兩年的獎金發放情況,今年發60個月年終獎是大概率的事情。
今年年初,因2021年公司大賺,長榮海運給員工發放了40個月的年終獎。當時有長榮海運員工在社交媒體上發聲,表示自己只是一般小職員就拿到40個月了,同事們也都是這樣,如果遲到早退的可能是36個月。還有長榮海運員工人在社交媒體上說「從來沒看到這么多錢!」
疫情3年來,一些長榮海運員工2020年領10個月年終獎金、2021年領40個月年終獎金加10個月年中分紅,今年若領到60個月年終獎金,等同3年領120個月。「3年抵10年」絕非坊間傳說,而是確有其事。(關于長榮海運,風馬牛之前寫過,可點擊這里閱讀)
02
盛衰交替,繁榮與蕭條都不會太久
在疫情中逆勢上揚的行業并不算太多,航運算是其中一個。
相比于長榮海運,有「海運茅」之稱的中遠海控,盈利能力更勝一籌。據媒體報道,中遠海控在近兩年時間里業績不斷刷新紀錄,其盈利已經遠遠超過公司開辦以來的盈利總和。
僅在今年前三季度,中遠海控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已經達到了近千億元人民幣,這比去年一整年賺到的892.96億元還要高。
作為典型的「強周期性」產業,最近這幾年,航運業迎來了一個超級繁榮期,羨煞一眾行業。
有繁榮,就難免有蕭條。
如果往回看,在那些行業蕭條的歲月里,因為誤判了行業周期的變化趨勢,逆勢而為,最終損失慘重的企業也不在少數,那些企業的掌舵者們,則經歷了各不相同的大起大落的人生。
香港過去有「四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剛、趙從衍、曹文錦)一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航運業進入一個較長時段的衰退期,「四大船王」中,董氏家族和趙從衍家族的航運公司都在那時陷入危機,欠下巨額債務。
當時,董氏家族的東方海外一度欠下200多億港元的巨額債務,1986年之前的一段時間里,隨時面臨破產清盤的命運,最后獲得霍英東的幫助才渡過難關,到1991年才扭虧為盈。
趙從衍家族的華光船務也在八十年代后期一度負債67億港元,并在香港交易所停牌。趙從衍誓死保華光,忍痛割愛,拍賣數百件家藏古董,并出售地產業等集團非骨干業務,獲取資金,同時展開資產重組,歷時數年,直到1992年才還清巨債。
03
一個行業巨頭的興衰史
相比于「香港船王」們苦心孤詣地「渡劫」,并且自救成功,在八十年代那場航運業大衰退中,有「孤獨之狼」之稱的日本三光汽船公司破產案,更加轟動一時。
香港「四大船王」的事業,基本上都起步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日本三光汽船公司的歷史還要早一些。
三光汽船創建于1934年,一開始只有兩艘船。1937年河本敏夫就任社長后,公司逐步壯大,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隨著世界貿易量大增,三光汽船快速發展起來。
在河本的帶領下,三光汽船從六十年代中期起,實行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經營方針。
當時,日本政府對航運業介入頗深。1964年,在日本運輸省的指導下,日本航運界建立了「海運集約體制」,將日本眾多航運公司組合成6大航運集團,這樣既可以加強日本航運業的國際競爭力,又可以使中小航運企業在政府和大企業的照顧下得以生存、發展。
但三光汽船既不要日本政府的扶植,也不接受日本政府的約束。野心勃勃、自行其事的作風,讓三光汽船在業界贏得了「孤獨之狼」的稱號。
上世紀七十代初,世界航運業進入黃金發展時期,三光汽船在1971年11月至1974年1月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連續籌集了總額912億日元的巨額資金,大量向船廠訂造油輪。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同行們在日本政府的指導下紛紛實行減量和多元化經營,唯獨三光汽船公司篤定「石油熱很快就會再次出現」,在船價下跌的情況下繼續購買船只。
這種「賭博式」經營給三光汽船帶來了豐厚的受益。隨著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波的逐漸消逝,船價回升,三光汽船賣掉一批船后大賺了一筆。
1964年,三光汽船擁有的船舶總噸位僅28萬噸,到1976年,已經增至2463萬噸。
然而,成功的經驗未必可以復制。迷信過去成功時的經驗,也許正是一場巨大失敗的開端。
七十年代后期開始,世界航運業,特別是大型油輪運輸業景氣指數明顯下降,三光汽船的決策者們卻還沉浸在之前的成功經驗里,對下降的趨勢沒有清醒的認識。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后,三光汽船不僅沒有及時收手,反而繼續擴張經營,想借機再撈一筆,還簽署了當時航運史上最大規模的訂貨單——購買125艘散裝貨船。
想象中的大型油輪的美好前景姍姍來遲。世界貿易量不斷削減,貨運價格隨著下跌,而運輸船卻有增無減,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航運公司風雨飄搖,大面積虧損。
1981年,三光汽船成為日本虧損最大的企業。
此后幾年,隨著新船訂單的持續交付,而經營不見好轉,三光汽船債臺高筑。雖然采取了諸如賣掉舊船、增發股票、公司改組等自救措施,但公司泥潭深陷,「良醫難救」。
此時,早已辭去三光汽船公司職務,投身政界,擔任過通商產業大臣、經濟企劃廳長官等多個內閣職務的河本敏夫也親自出馬,到處游說為公司籌集資金,也無濟于事。
1985年8月,失去銀行資金支持的三光汽船只能宣告破產。
破產前,它擁有的船只登記總噸位一度占日本船舶總噸位的六分之一,世界船舶總噸位的百分之三。
破產時,其負債總額高達5200億日元(當時約合21.7億美元),是當時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企業破產事件。若加上拖欠貿易商社及根據租船合同應付的金額,其負債總數則超過了1萬億日元。
如此一家大公司的倒閉,在當時的世界航運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由此產生了巨大的連鎖反應,多家相關企業跟著倒閉,三光汽船的「后臺老板」河本敏夫也不得不辭去內閣職務。
隨后,三光汽船破產重組,找到了新的投資人,重新回到航運市場中來。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公司經營逐漸好轉起來。
2003年,沒有吸取破產教訓的三光汽船又開始采用激進的擴張策略,大肆擴展船隊規模。
由于三光汽船風險管理能力不足,其業務結構中,即期及短期合同占據較大比例,在航運市場繁榮時,獲利很多,一旦航運市場急轉直下,公司現金流快速減少。
2007財年,三光汽船銷售收入2290億日元,利潤710億日元。到了2011財年,隨著全球海運量下降,航運市場運力過剩,運費大幅下降,三光汽船的銷售收入下降為996億日元,虧損313億日元,加上船舶減值損失等非經常性損失,共計虧損1104億日元,再一次成為日本虧損最多的航運公司。
2012年,三光汽船的負債又一次達到了20億美元。因其欠債累累,一些船東采取扣押三光汽船船舶的方式迫使其選擇啟用債權人保護和重組程序。
其后,三光汽船通過大幅削減船隊,完成了第二次申請破產交易。到2014年年底完成破產重組時,其船舶數量僅余28艘,與2012年宣告破產時期的200艘左右相去甚遠。
兩次破產重組,讓這家曾經的行業巨頭元氣大傷,雖然近年來還在經營,但規模和行業影響力早已式微。
04
「人生致富靠康波」,企業呢?
三光汽船的兩次破產,固然與其自身發展策略和經營能力有關,也與行業的興衰周期有很大的關系。
航運業務作為全球貿易的重要載體,是經濟的「晴雨表」。其行業特點決定了,行業里的所有企業,既要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上與其它企業競爭,又得時時刻刻盯住世界宏觀經濟,以追隨行業周期的腳步。
都說「人生致富靠康波」,企業的成敗,又何嘗不是隨著興衰周期起舞的結果。要么順應周期,乘勢而為,要么逆之而行,在競爭中丟盔棄甲,甚至破產出局。
只不過,周期的輪替,興衰的轉換,變數都太多。個人也好,企業也罷,想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跟對趨勢、抓住機遇、成為幸運兒,實在是太難了。
參考資料:
1.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計劃裁員1萬人,最快本周開始,中國新聞網
2.傳長榮海運年終獎金60個月:現在談為之過早,聯合早報
3.香港世家,趙氏船王沉浮60年,人民網
4.回望百年中國大家族系列之七:「世界船王」接「2」連「3」,新聞天地
5.「海運茅」中遠海控三個季度賺近千億,拿出400億元買船買港口,界面新聞
6.三光汽船破產風波,中國船檢
7.三光汽船公司倒閉始末,航海
8.日本最大的企業倒閉事件——三光汽船公司破產,國際問題資料
9.三光汽船將重建船隊,中國船舶工業經濟與市場研究中心
10.1985年以來世界航運周期分析,世界海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