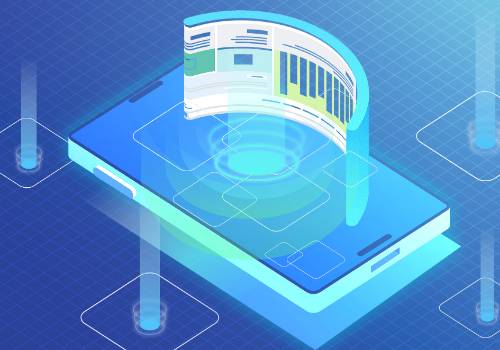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頁 >綜合 > 公司 >
阿來:流寓蜀中 杜甫仍然不忘“憂國與懷鄉”
四川在線記者 成博 肖姍姍 阿來書房供圖
8月26日下午1點,由川觀新聞、封面新聞、上行文化主辦的阿來“杜甫 成都 詩”系列講座迎來19講。本場講座中,阿來以“憂國與懷鄉”為主題,再次深入杜甫的內心世界,展現一代“詩圣”詠史懷古、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
 (資料圖)
(資料圖)
講座現場
“過去幾期我們講杜甫詩,主要是貼近成都來講,講他在成都的生活、成都時局變化對他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影響。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是不是他所有對現實對時事的關懷都是發生在眼前?”講座開始,阿來介紹這一期的主題如何確定,“在成都期間,他其實也是心系北方、心系朝廷。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講,心系朝廷其實也就是心系天下、心系國家安危”。本期講座中選取的《登樓》《黃河二首》《大麥行》《天邊行》《憶昔二首》《至后》《恨別》《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作品,就是杜甫流寓蜀中,仍然不忘“憂國與懷鄉”的證明。
初到成都時,杜甫曾寫下《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春日成都繁盛的花事令飽經北方戰亂的杜甫感到欣喜,但到了《登樓》中,杜甫觀花的心情變成了“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阿來表示:“成都的社會環境雖然相對安定,但在當時,國家正處在‘安史之亂’以來頻繁的戰亂之中,不光是安祿山作亂打亂了北方大局,各地軍閥也在兵變,這引起了客居成都的杜甫更復雜的情感跟心情。”面對“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的時空情境,無可奈何的的杜甫,想到了那個遇到劉備之前、在隆中有些懷才不遇的諸葛亮,每日只能通過吟誦傳說是諸葛亮所作的《梁甫吟》來排遣心中的情緒。
除了天下動蕩、感時憂國,杜甫在蜀中所切身經歷或聽聞的兵災更觸發了他詩人的悲憫。《黃河二首》中吐蕃擊敗海西軍侵入長安、供應前線導致蜀中百姓家沒有余糧的景況杜甫都看在眼里、聽在耳里,他期待著有一位賢能的君王能夠消弭戰亂,他發出了“愿驅眾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的感嘆。“杜甫了不起,他那時候看到要解決天下紛爭,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放下文化差異、放下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別,大家書同文、車同軌,建立同樣的文化信仰,最后建立高尚的道德,基于共同的國家信仰才能平定這種紛亂不休的局面。”阿來說。
到了《大麥行》中,杜甫寫到了今天巴中、漢中一帶,大唐軍隊與諸羌軍隊之間“搶秋”與“防秋”的拉扯。“大麥干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眼看豐收在望,當地的男男女女卻并不高興,“秋天莊稼成熟了,不等農民收莊稼,雙方的軍隊都出動去搶莊稼,誰能拿到糧食誰就好說,”阿來說,杜甫注意到,當地無力保護當季收成,所以“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士兵們從成都出發,又一次遠離家鄉去與敵人戰斗。“杜甫寫這首詩,既同情當地的老百姓,也同情這些士兵和軍人。”
但是,在憂國與懷鄉的情緒驅動下,杜甫也不是只有沉郁,當他聽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想著可以返回故鄉時,也曾經有過“漫卷詩書喜欲狂”的時刻。“大概762年、763年的時候,杜甫聽到安史之亂被平定的消息,后來證明這是一條假消息,但對當時的杜甫來說,這條假消息也令他激動了很久,并且寫下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阿來說,“在成都的時候,杜甫經常說自己老了,但當他以為自己終于可以回到河南老家的時候,他說的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五十多歲的老頭,突然覺得自己還年輕了。”
講座現場
講杜甫的憂國與懷鄉,阿來認為,這些作品透露出一種“史詩”的氣質,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阿來引用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的話說,史詩重要的精神氣質在于人的“不懈”。“危難時,堅韌不拔是不懈;安定時,發現美——事物之美,生活之美,也是一種不懈。這也是某種英雄主義,中國古人稱之為‘九死未悔’。蘇東坡更有‘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詩句。”阿來表示,“拋頭顱灑熱血,是英雄主義。如司馬遷般忍辱負重,完成自認為的天賦使命也是一種英雄主義。而杜甫顯然就是后一種英雄主義。我們今天讀杜甫,讀他的憂國詩、懷鄉詩,除了讀出當時時代的悲愴、他個人生存意味之間的那些尷尬以外,更要從他的詩里得到那種經過升華的,從語言到情緒、到我們國家意識、文化意識的那種美麗。”
據悉,本場講座也是本系列的倒數第二講。從2022年2月12日,杜甫1310歲生日那天,到2023年8月,讀者們跟隨阿來的腳步,穿越古今,見證了杜甫在成都的喜怒哀樂,起落沉浮,更見證了大唐的昌盛興衰。